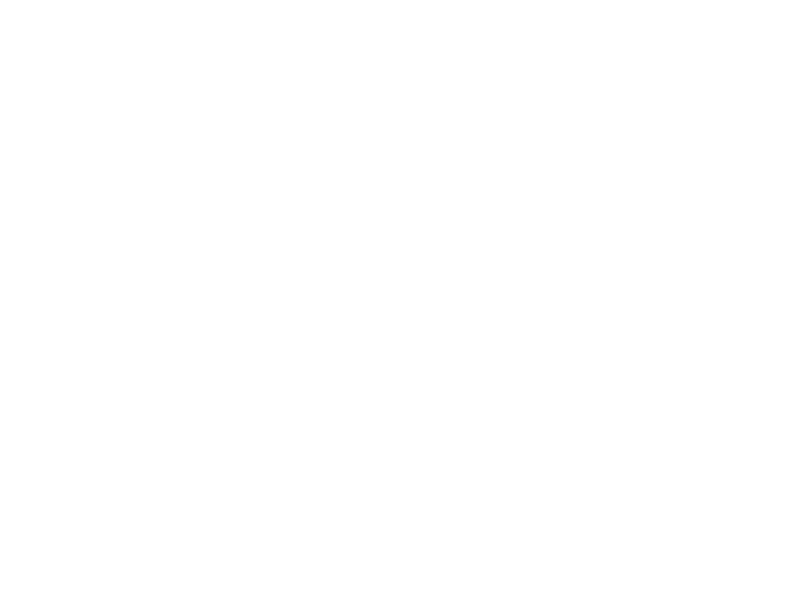今天有這樣的機會報告這一個個案,其實也是在報告我在治療憂鬱症的心得,提供大家多一點的空間想像,讓藥物在治療的空間可以發揮彈性,避免陷入僵局,最常見的僵局就是—醫生,我不是憂鬱症嗎,我不是在吃藥了嗎,為什麼不會好?
從我開始學習精神分析心理治療,有幾個轉折。以前總認為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的界限是壁壘分明的,這也是在初學時會理解到心理治療和藥物治療的部份是不容易彼此對話的。當然一部分也反映了我對心理治療的敬畏之意,因為不熟悉所以就保持距離,小心的操作,這其實也是常見的防衛反應。等到當了主治醫師,第一線接觸到越來越多的精神官能症個案,曾經一度讓我心力交瘁,因為藥物的極限,常常逼使著自己去思考心理治療的角色,偏偏我所認識的精神分析又是充滿了浩瀚的知識,就這樣卡在十字路口,還好,這一年到倫敦去,做了一些沉澱,也更接近的精神分析的成熟國度,”疏通”比起”防衛”真的好多了。學習用精神分析的角度去觀察自己在臨床與個案、個案家屬、藥物、工作人員互動的動力,可以給自己有一些撥雲見日的感覺。有時我就像一個陪伴者,有時像個裁判者,有時像個代罪羔羊,有時又像一個救世英雄,這些被投射的不同化身,不在於當什麼像什麼,而是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回饋到治療情境中,等待適當的時機,啟動個案的了解。所有的精神官能症一定都有關係上的運作,進而影響醫病互動、藥物的效力、與對病徵的解讀。藥物確實透過神經傳導物質,改變了古典精神分析理論中潛意識的能量程度,讓原本應該要啟動的釋放機制得以平衡,但是在心靈內在、人際衝突、人格成熟的領域遇到了極限,相對的開藥的醫師,這一個變相在某種程度主導了這一個藥物極限後的反應,正如同感冒藥可以治療感冒,但是改變體質需要合併更長久的治療模式。